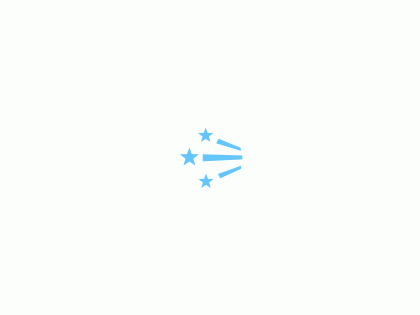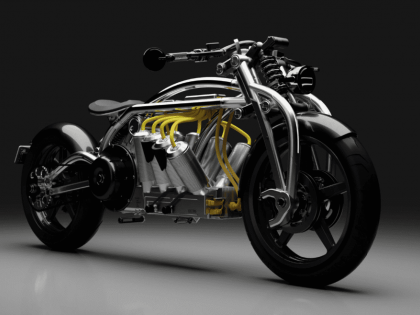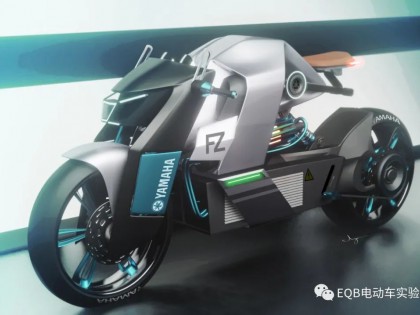最近广州市拟立法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等“禁售”、“禁油”、“禁行”、“禁停”、“禁坐”。
广州于2007年1月1日开始全面禁摩禁电。之后道路上摩托车、电动车锐减,但并没有完全绝迹——媒体报道用“死灰复燃”、“屡禁不绝”来形容这一状况。
2006年年底一纸通告就禁摩禁电,尽管当时舆论沸腾,但无力回天。甚至,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也似乎遗忘了此事。而媒体带有道德倾向“死灰复燃”、“屡禁不绝”等的形容,显示的恰恰是那些必须完全依赖于电动车谋生者的无奈和无助——快递行业、游荡于地铁口、批发市场搵食的市民、做小生意的小贩,他们不得不冒着“违法”的风险,奔波于这个城市之中,像做了亏心事的蝙蝠,躲避着官方的执法,内心惶恐。
我们必须承认这么一种现实,舆论及市民的力量还不足以抗拒或阻止权力按照其逻辑行驶,如果权力愿意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予取予求的局面。因此,如果现实点来考虑,确切地说,应该是犬儒地想,若当局没有行政洁癖的话,保持这个默契,局面至少还是可以接受。
舆论善良地认为,不再去纠缠官方的禁摩禁电决策,是否与保障市民自由选择出行交通工具的国家法规相抵触、是否构成对合法生产摩托车电动车产品企业事实上的行政封杀,是否是对已通过合法途径购买了摩托车电动车的市民的财产的变相剥夺——至少保持这种局面是“多赢”的:争议搁置,人们在禁摩禁电之后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官方可以继续去宣传它的禁摩禁电成果并在面对争议时像陈建华市长说要权衡利弊巩固禁摩禁电成果以宣示政府的坚决态度;有条件的市民会因为当局的禁摩禁电政策选择其他出行方式,路面上摩托车电动车会因此大量减少,这可以成为当局权威以及政策有效性的佐证;而那些不得不依赖摩托车电动车谋生的市民,则与官方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并期待官方能够枪口提高一公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彼此心照不宣不至于断绝他们的艰难谋生之路;而当这个城市有重大活动或者庆典时,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暂时消失——如同那些摆摊的小贩一样,以免给当局添乱,满足某些人对这个城市秩序的洁癖想象。
然而,看来有人对目前这种现状不满足,或者是担心失控,他们希望通过立法,把摩托车电动车等“赶尽杀绝”,彻底清理出广州市场。单纯的道路执法的威慑作用看来已经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因此需要在源头上“斩草除根”——其实要是允许的话,他们也许会直接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企业关停,可惜这些企业是合法企业,这是一个城市的主政者鞭长莫及的地方,他们惟有仰天长叹,于是,“禁售”、“禁油”、“禁行”、“禁停”、“禁坐”——这可是他们的地盘,让这些摩托车电动自行在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立锥之地,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目的!权力的懒惰、傲慢和嚣张彰显无遗。
不过,也许他们意料不到的是,其实在2006年底那场关于广州禁摩禁电的讨论,由于时间的仓促及官方对信息传播的干扰,讨论并没有充分展开并深入,如今借助这次强化禁摩禁电要全面封杀的立法,舆论开始重新拷问当初禁摩禁电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从舆论的反应看,对禁摩的争议似乎远没有禁电那么大。因此为表述方便,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主要集中对是否该对电动自行车“赶尽杀绝”,而这并不意味着苏少认为禁摩就不存在类似的问题。
考量这个问题有两个维度:一是尊重市民的需求,根据广州的实际情况,依照国家相关法规对电动自行车进行规范。这一点广东省政协委员杨中艺先生一直在不懈努力。2013年他就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在省两会期间提交提案,由此也带来“电动车是否解禁”的讨论,可惜之后在广州市长陈建华“权衡利弊巩固限摩限电”的表态后不了了之;一是用更严格的政策包括更严厉的惩罚,抑制市民的需求,以减轻官方所称的“单纯道路执法的难度”达到更好的执法效果。
对于后者,同样一直不乏有人在为此孜孜不倦努力着。通过媒体、人大代表抱怨“禁行不禁售,电动车难禁”、“禁行不禁售,累苦的只能是执法人员”,到如今试图通过立法一了百了,这其中的逻辑,读者诸君可仔细琢磨。
那么,问题就来了:
第一问:究竟是怎样的政策初衷、出于何种政策考量,促使官方无视市民的谋生需求铁了心要断绝他们的谋生之路,将电动自行车“赶尽杀绝”清出广州?
第二问:在公民的日常自由与方便以及官方管理、执法的方便之间,为何官方毫无例外选择了管理、执法方便?如果这不是懒政,不是缺乏对民生艰难有感同身受,是什么?这是一个声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该有的态度和行为吗?
第三问:广州市长陈建华在回应广东省政协委员杨中艺提案时说,“权衡利弊巩固限摩限电成果”,那么,广州禁摩禁电的成果是什么?官方是否有这么一份成果的报告?能否向市民公开这份报告,让市民明了官方的苦心孤诣,并响应官方的号召继续一同巩固这一成果?
第四问:2006年底,广州市公安局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广州市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禁行通知和处罚方案”。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老先生就从决策的程序问题指出,禁行电动车,开个通报会就行了吗?认为禁行缺乏法理支持,要求人大审查该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如今广州法制办立法征求意见,王则楚老先生认为,即便是立法,也不能只是开个听证会了事,其严格属于重大事项应交由人大讨论并决定。按照2009年修订2010年1月1日起实施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中第二条规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侨务等工作的重大事项适用本办法;而第四条,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重大事项,应当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其中(一)就提到,“贯彻执行宪法、法律、法规……的决议、决定的重大措施”,毫无疑问,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严格属于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而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出台,《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广州市法制办试图通过地方部门立法全面封杀电动自行车,这必然涉及到广州如何“贯彻执行宪法、法律、法规的决议、决定的重大措施”,那么,是否该严格按照《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的规定,交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第五问:2011年6月16日,时任珠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张强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在被问到“珠海对电动车为何只禁行不禁售”时回应说,“电动自行车销售问题,属于行政许可法调整的范畴,准许销售电动自行车,与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并不矛盾。因为商家可以面向外市销售,本市一些大型住宅小区内部巡逻,对电动自行车也有需求。”对于这位兄弟城市公安副局长的说法,广州市政府有何看法?若商家只把电动自行车卖给外市的顾客,政府有什么权力或合法依据禁止其销售行为?
第六问:在2013年那场关于是否开禁电动车的讨论中,时任广州市交委主任冼伟雄先生断言,开禁电动车是“历史倒退”。姑且不说国际上诸如巴黎东京这些大城市没有禁摩禁电,国内北京上海等城市也没有禁电,广州就比它们“进步”?
冼先生的理由是,广州道路资源增长有限,若再增加一种占用道路资源的个体出行工具,势必增加公交发展的难度。要发展公交,就得剥夺市民选择个体出行的自由?这是广州自行车道建设至今严重滞后的真相吗?若就人口密度、道路资源、车辆保有量来比较,日本东京,人口1300万,与广州差不多;东京的面积只有2155平方公里,广州的面积则是7434平方公里;东京机动车辆的保有量则接近500万辆,广州则刚超过200万辆,只有东京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东京为何还能“历史倒退”不禁电呢?
第七问:2007年全面禁行的主要理由是因为“两抢”犯罪肆行。客观来说,禁行之后广州“两抢”犯罪行为急剧下降。但同时可以看到,即便在国内那些没有禁摩禁电的城市,“两抢”犯罪的行为同样在减少。那么,问题来了:这究竟是社会发展导致犯罪形态的演变,还是全是禁摩禁电之功?退一步来说,即便基于安全考量,为打击“两抢”犯罪不得已必须禁摩禁电,那么,如今使用摩托车电动车者,有多少是进行合法谋生工具之必须,又有多少是用来作为“两抢”的犯罪工具?
第八问:禁电的一个理由是污染问题。说实话,这属于专业话语讨论的范畴。只是,从常识来说,电动自行车行业有国家标准,电池会污染环境本身,不足以成为某个城市可以单独在其城市内对其全面封杀的理由,更何况即便会污染环境的电池,同样也可以通过无害化的技术处理得以解决。而从技术原理上,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蓄电池与电动汽车使用的电池不会有太大的本质区别,那么,如何解释广州的不少领导都盛赞电动汽车“无污染”?仅仅因为汽车企业能够给广州带来GDP和税收,而电动自行车不行吗?
第九问:2013年3月30日,《广州日报》以《禁行不禁售难禁电动车》为题的报道中,专门罗列了电动自行车的四宗罪:超速、抢道、火灾,伤亡。如果超速抢道包括造成交通伤亡可以成为将其全面清出广州的理由的话,那么,恐怕没有哪种交通工具可以在广州生存。面对这种情况,究竟是该用交通法规对其规制,还是一禁了之?至于电动自行车的技术标准是否不符合现实的要求容易造成火灾,技术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完善来解决,一禁了之更没有理由。
第十问:广州现在汽车限牌限购,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就要全面封杀“赶尽杀绝”,自行车道建设就严重之后。倘若按广州交委原主任冼伟雄先生所说的,是为发展公交腾出道路资源,相信最终目的是为了治理交通拥堵,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来了,抛开所有关于自由权利的争议,市民现在就为了治理拥堵这一目标配合政府,那么究竟广州需要多久,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抑或多长时间就可以完成治理拥堵的目标?如果在这一时间内仍然无法达致政策目标,作为决策者,包括作为交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陈建华市长,需不需要承担责任?该承担怎样的责任?